研究院动态 首页» 研究院动态
2021-05-08
程水金教授:《尚书》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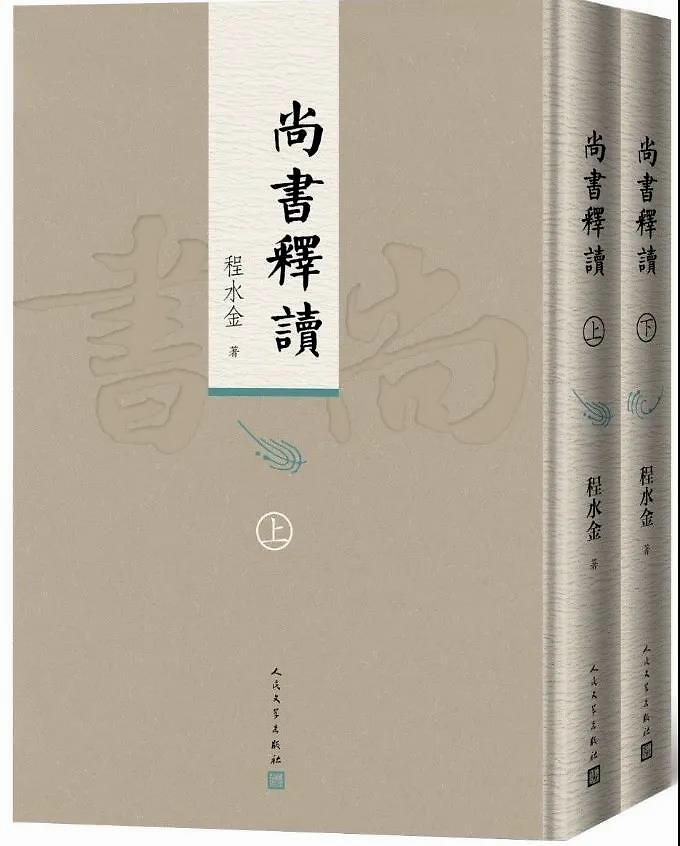
《尚书释读》,程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
【前 言】
《尚书》是中国古代第一批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文献,大约最初只是以单文为篇卷,在学人之间辗转传抄。即使是秦代整编《尚书》,也可能衹是作了篇目的取舍,并非如后世结集成书。而历来讨论较多者,是关于《尚书》在秦汉以后的流传与授受情况。所谓故秦博士伏生以及西汉欧阳与大、小夏侯所传授之今文,景帝初年鲁恭王刘余所得之孔壁古文逸书,以及东晋豫章内史枚赜所上之伪古文,诸如此类有关《尚书》学史的研究及其结论,也基本一致,并无大的轇葛。
唯其作为王室档案文献的上古之书,本应藏之于王朝内府秘室,何以于先秦之世便逐渐流于一般士子学人之手?且其书既为“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则皆为官方政治文诰,而历虞夏以至周初,倘若虞夏之世即有文字应用,则此类官方文诰之多,当更仆难数,而秦博士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加上孔壁所出之“得多十六篇”,亦不过四十五篇之书。即使如孔壁所出之《书序》以为“书有百篇”,与悬想所当有的王室内府档案文献相衡较,其数量不也仍然显得过于短少?而且《尧典》、《臯陶谟》以及《禹贡》、《甘誓》等,所谓虞夏之书,何以反较其时代远在千有余年之后却“诘屈聱牙”的周初文诰更加易于诵读?
凡此诸多疑惑,无非指向二点:其一,《尚书》各篇文本成书的年代先后;其二,《尚书》各篇文本流传的历史原因。关于第一点,前人论述较多,其观点容或稍有参差,但看法大抵一致,即其文所涉之史实年代愈久远,其成书年代则愈晚近。因此,这第一点疑惑,迄今已不复为疑惑了。至于第二点,亦即这些尘封在王室秘府的档案文献,是凭着什么理由却在两周之际逐渐流于一般学人之手?其间的历史机缘究竟是什么?而且与此相关,那些事涉遥远的传说时代且神话与史影尚无明确分际的虞夏之书,又何以要在王室档案文献广为流布于学人之手以后方始造作成书?这些流传者或曰编纂者到底想通过它们来说明什么?这些问题,无论帝制时代的经注家,抑或近世以来研究《尚书》的学者,概无论及。
笔者曾于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九卷第一期(2001年6月)发表过题为《西周末年的鉴古思潮与今文〈尚书〉的流传背景——兼论〈尚书〉的思想意蕴》的文章,就上述问题提出了一孔之见。这篇文章,是根据笔者当年(1997)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褚斌杰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提交的学位论文之第六章《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第一节《鉴古思潮翻开了尘封的历史档案——《尚书》的流传背景及其思想内蕴》改写而成的。《汉学研究》编辑部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说:“《尚书》有不少篇章作于周初,由周初至春秋时代的流传情形,历来论述相当少,盖因相关材料阙如的缘故。本文作者试图从西周末年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时代所产生的鉴古思潮为基础,来推论《尚书》篇章的流传,在方法上可说是一种创新,也解决了西周时代《尚书》流传情形的部分疑惑,此点对《尚书》流传史和经学史都有一定的贡献。本文另一重点,即归纳《尚书》中的思想意识。作者以为《尚书》中有:(1)‘人唯求旧’的稽古意识;(2)‘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3)‘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识。此一论点,以前学者也曾论及,但本文的归纳,显然较有系统。”审稿专家的这些看法,无疑对本人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结论作了充分肯定。同时也说明,本人所采取的研究路径也基本上是正确的。
不过,就本人研究的整体理论架构而言,《尚书》在先秦的流传,只是叙述了一个局部的枝节问题,或者说,仅仅是某个文化类型在其自身观念形态的历史运作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已。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已于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的多卷本学术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之分论第二编《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部份(见该书第一卷)。笔者认为,先秦思想文化与散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巫卜文化与巫卜散文、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士人文化与士人散文三个类似于板块推移或蝉联蜕变式的发展阶段。而博士论文衹是有关第二大板块亦即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的研究与叙述。
置于这个板块推移的文化变迁大势的观照之下,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早期史官文化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来说,也就是中国早期史官的身份及其职业特征,经历了一个从巫史同源或曰“巫祝之史”,到“起文书草”亦即“作官书以赞治”的“胥吏之史”,再到执简策以记言行的“记事之史”的漫长演变道路。与此同时,史官的身份特征及其具体职掌的每一步历史分化,无不昭示着史官文化的观念形态及其思想内蕴的不同心路历程。从“胥吏之史”的分化到“记事之史”的产生,必须以“传世与不朽”的观念为前提。而“传世与不朽”观念的实现,可以有不同途径,从而导致了由铸器勒铭到着之竹帛的载体演变。且“记事之史”的分化与记事简策的产生,又为编年史书的问世预设了史料前提,也提供了历史反思的经验对象。
刘知几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定成篇,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刘子玄所谓“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正是史料与史学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过,从“当时之简”到“后来之笔”,虽然是“前后相须”,但其间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岁月,也伴随着艰苦的思想历程。也就是说,从记事简策的档案积累到编年史书的删定勒成,必须经历从“以古为鉴”到“历史反思”的观念飞跃。而且,在“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观念运作过程中,其“以今逆古”与“以古鉴今”之“当下”与“历史”的双向互动关系又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展现形态。即始而“援例性”的以事为鉴,继而“抽象化”的以理为鉴;再进而“事理相融”的“理事共鉴”;于是也将“当下”与“历史”的观念互动推向了史官文化在“以古为鉴”这个思想环节中的最后阶段。确证这三种不同的观念互动形态之所以存在的文献依据,就是传世的《尚书》、《逸周书》和《国语》。其各自的文本特征,正好体现着与“事鉴”、“理鉴”与“理事共鉴”相对应的成书目的。
时过二十余年,虽然在《尚书》个别文本的具体阐释上,乃至在某篇个别文句的具体释读上,容或有所不同;但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这次全面整理释读今文《尚书》的过程中,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这个思路与方法不仅使我对《尚书》大部分篇章的流传背景有了比较直观的感受,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推断《尚书》某些文本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关概念必须事先厘清。如前所述,由于在“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观念运作过程中,存在着“历史”与“当下”的双向互动关系,因而所谓“《尚书》的年代”就是一个内涵并不十分准确而且其边界也相当模糊的概念。也就是说,所谓《尚书》的年代,至少有如下几个不同的意义指向:一,史实年代;二,成书年代;三,流传年代;四,整编年代。职是之故,则某篇《尚书》文本的史实年代并非就是它的成书年代;因而其成书年代既然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实年代,却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传年代。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某种最初的传播动机直接促成了某些相关文本的新生与定型,因而其流传与其成书,或者其成书与其流传,二者恰恰就是并时共生的。
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以《尚书》的几个具体篇目为例,对《尚书》文本在“历史”与“当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各个《尚书》篇目在“年代学”上的各种不同情况,略作说明。
众所周知,幽王死于骊山之后,平王即位而东迁洛邑,这是西周春秋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尚书》中的《盘庚》、《召诰》、《洛诰》甚至《康诰》篇首四十八字,无不与之相关。如果我们从“年代学”的视角加以考察,则各篇的实际情况便相当复杂,因而也不能一概而论了。
《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盘庚》的成书年代竟在周室东迁之际,但可以肯定的是,《盘庚》三篇从王室档案流于学人之手,一定与平王东迁洛邑密迩相关。至于其具体文本在西周末年从王室档案流播而出的过程中是否有所异动,则不能确指。然而今传《盘庚》三篇的文本次序,与其相应的史实次序颇有些颠倒,却是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今之下篇应为上篇,今之上篇与中篇,依次当为中篇与下篇。这种文本与史实相乖舛,并不难察。之所以如此,是否与其流传的先后次序有关,或者表达了流传者的某种另外的现实意图,其详情今一概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无论其成书之年究竟在哪一代商王,这并不重要;但倘若我们认为《盘庚》三篇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商代成书之时的初始面貌,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因此,罔顾上下文的具体语境,简单地用殷虚甲骨文的个别用字以替换与曲解《盘庚》中的一般用字,则无异于刻舟求剑,亦自郐无讥而已。
毫无疑问,《召诰》与《洛诰》二篇,也应该是与平王东迁洛邑直接相关的文献。至于其具体的成书年代究在何时,却不能根据它们所指涉的史实年代作判断。
首先,正如前辈学人所指出,二文虽以“诰”名篇,但在文体上却与西周初年典型的“诰体文书”如《大诰》、《康诰》、《酒诰》之文大不相类。其次,就作“诰”的时间与二篇文势而言,郑玄从伏生《尚书大传》之说,以为《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之时。但清人皮锡瑞不茍郑说,认为“二篇文势相接,不得以为相隔二年”。第三,二篇所记成王、召公以及周公的相互谈话,其谈话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话的主体与谈话的对象,都十分混乱模糊。尤其是《洛诰》一篇,近人金兆梓说,“此篇开头倒也明白记载着两人一往一来的对话。但于周公二次发言后,却紧接着记载周公三次发言。已令读者觉得周公一人在自言自语了。周公三次发言后,忽又接连记载成王一连四次的发言,更好像两人都各在自言自语,有类白日梦呓,致使读者如堕五里雾,连他两人在说些什么也搞不清楚。这样的记载方式,疑未能辨出两人的对话应孰先孰后而机械地将两人的语言各各分成两大堆之所致。这样的安排似乎比偶尔的错简还错得更严重而荒诞”。于是金氏便依照他自己的想法,将《洛诰》原文大段改编重排。舛乱经文,却自认为“给它理出一个头绪”。至刘起釪氏作《尚书校释译论》,则依据清儒朱骏声之说,亦移“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一句于“王入太室祼”之下。其所以如此纷纷改纂原文,皆在以“诰体文书”为标准,调整与解决文本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时空错乱感。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洛诰》与《召诰》所载之史实与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之事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则不能排除其在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之际据源文件材料缀合成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确定二篇的流传时代正是它们的成书定型年代,则上述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洛诰》各节各段所言之旨,不外乎反覆强调洛邑营建之慎重及其镇抚殷遗、管控东土之政治目的。至于周公与成王各自的说话时间、说话地点以及他们各自谈话的具体对象,则并非西周末年的缀合者所特别关注之事。而且本篇并非首尾完整的“诰体文书”,不过是替平王东迁的当下行为寻找历史依据而已。也因此,《洛诰》文末“王命作册逸祝册”以及“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云云,此虽为《尚书》中唯一记载预事史官之名及其叙事时间背景的文字;但也不过等同于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而已,与文本最后编排与写定的时间并无直接关涉。之所以如此编排缀合,无非是要增强历史的真实性与厚重感,为平王东迁的当下行为堆积更多的历史筹码。正如《召诰》并非纯为“召公之诰”,其所以以“召诰”名篇,也不过是为东迁增加除周公之外的另一个重量级历史人证而已。唯其如此,则二篇文档在西周末年的阅读价值便可以充分有效地实现了。而且,随着平王东迁行动之告终,本文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也就圆满地完成了,至于那些淹没在时间长河之中的历史细节,对于西周末年的编纂者而言,也就没有深度打捞与细心钩沉的必要了。
由此可见,从《召诰》、《洛诰》的流传背景来看,二篇成书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自始至终皆在凸显当年洛邑营造过程之慎重,其地理位置乃经由二代周王及周公与召公二位涉事大臣之反覆抉择,以及屡屡申说周王朝“其自时中乂”之管控意识。因而无论是史实指陈,抑或是主旨申述,在在皆是替平王东迁洛邑作历史辩护与文献支撑。虽然召公之诰成王,周公与成王之对答,周、召二公之交谈,以及册命“周公后”诸多事宜未必同在一时,或在摄政五年营成周之际,或在摄政七年周公致政之后;但整理流传者的现实目的既然都是针对平王的东迁,那么,因其同时成书,以致“二篇文势相接”,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当然,档案材料的原始作意,与后来编排缀合的主观取向,未必全然一致。这也是《洛诰》篇首“复子明辟”及其相关文句之解说乃至全篇主旨之理解历来衆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职是之故,本书对这两篇文本的释读,将档案材料之原始作意,与应时缀合成篇之现实取向略略作了辨析,以各还其真;同时也对学术史上某些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意见,是着眼于既往史实的解读,还是着眼于当下文本的串讲,也一并稍作辨析。至于是否妥当合理,读者诸君自可裁而定之。
此外,关于《康诰》篇首四十八字的错简及其归宿,也是《尚书》研究者颇感棘手的问题,自古纷纭衆说,迄今亦无定论。
《康诰》是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徙封康叔于妹邦的诰命之辞。根据《尚书大传》以及《左传》定公四年载卫人祝佗“命以《康诰》”之说,本篇当作于周公摄政四年,其大旨乃诰康叔“明德慎罚”。以“历史”与“当下”双向互动关系而论,西周末年之所谓“周召共和”的历史背景,或者是本篇之所以流传于后世的重要原因。因为西周初年的“摄政”与西周末年的“共和”,毕竟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但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这四十八字,却与《康诰》正文风马牛不相及,乃是与周公营建洛邑有关的文字。
如前所述,《召诰》与《洛诰》是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之际因档案材料整理成篇,而非西周初年之原始文档样态。凖此,亦不难想象,“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十八字其所以置于《康诰》之首,或者正是因了这四十八字,两周之际的学人竟以《康诰》为“营建洛邑”的文诰,从而读出了与平王东迁相关的现实意义,故而得以流传于世的吧!或者置此四十八字于《康诰》之首,竟然是出于东迁之际学人之手而其读写传抄《康诰》乃另有其意呢?此事颇可玩索,未始纯为“错简”而别无丝毫历史意蕴与文化符码存于其间。
果如此,则两周之际学人之读写传抄《康诰》,自当别有用心。于是“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便与“东国洛”之“新大邑”在地理位置上构成拱卫呼应之势。而事实上,平王东迁洛邑,卫武公亦参与其事,且大为有力。此或者竟是《康诰》较《伯禽》与《唐诰》幸运,从而得以于两周之际流传于后世所潜在的深层文化心理契机,亦未可知。否则,祝佗所谓“命以《伯禽》”而封鲁、“命以《唐诰》”而封晋,其作诰时间皆与武王及周公摄政建侯卫之时相去不远,何以彼二篇皆所不传?这就是说,既往之历史与当下之现实,可能会误打误撞,而后又在某一点上相互拍合,必然造成文本的严重误读。此庄生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毕竟文本误读虽然有时是偶然的、无意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误读者为着某种别样的目的而有意以为之。当然也毋庸讳言,文本误读,同样是导致思想流变与传统漂移之不可忽视的能动因素,而且还往往是更为重要的主体因素。
以上所述,是西周末年平王东迁洛邑的当下现实,与《尚书》之中相关度比较大的几个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这仅仅衹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但也足以表明我们整理释读《尚书》的全部理论依据及其思想方法。至于这个理论与方法,对于《尚书》文本的解读,是否自出机杼别有会心,是否触摸到解决《尚书》学史上迄今悬而未决的某些疑难问题的边缘,尚须读者诸君的悉心审查与时间老人的耐心见证。然而,这大抵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最后,关于《尚书》的篇目以及本《释读》的取舍与编排,也该一并作些交待,这也是《尚书》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近人蒋善国认为,司马迁“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之说,未必是事实。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可能就是秦季编定的《尚书》篇数。收入《秦誓》列于编末,既体现着以秦继周的正统思想,也是《尚书》在秦末最后编定的铁证。
然而,关于伏生《尚书》的篇数,却发生了不小的争议。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王充《论衡·正说篇》也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于是伏生所传《尚书》之篇数以及其中有无《泰誓》,遂有多种说法。一者以为经文仅二十八篇,加上百篇《书序》,共二十九篇。明梅鷟《尚书考异》、清朱彝尊《经义考》及陈寿祺《左海经辨》等皆主此说。二者以为司马迁以后得之《泰誓》充伏生所传之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经集传》、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戴震《经考》等皆主此说。三者以为将二十八篇中之《顾命》分为《顾命》与《康王之诰》二篇。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龚自珍《太誓答问》、俞正燮《癸巳类稿》、成瓘《篛园日札》、皮锡瑞《经学通论》等皆主此说。四者以为伏书二十九篇本来就有《泰誓》。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刘师培《左盦外集·驳〈泰誓答问〉》皆主此说。上述四说,各有所依,又互有驳正。
新出《熹平石经》之《书序》残石,上连《文侯之命》,篇目下有“廿八”二字,则第二十九篇当为《秦誓》无所可疑。因此《书序》不在二十九篇之数,亦无所可疑。伪《孔安国尚书传序》说:“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是伏生今文《尚书》不分《顾命》与《康王之诰》二篇亦可知。《尚书大传》乃伏生解说《尚书》之语录,其中已载“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则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当有《泰誓》之文亦甚明,不待后得之《泰誓》乃有其篇。
《汉志》书类著录:“《经》二十九卷。”班氏自注:“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又录:“《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所谓“章句二十九卷”或“解诂二十九篇”,“卷”即“篇”,“篇”即“卷”,则大、小夏侯《尚书》经文皆二十九篇无疑。而《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欧阳经》三十二卷者,不为《书序》作章句而已。其所以《经》三十一卷者,因后得《泰誓》之文入其中,为便于区别,乃将伏书原有之《泰誓》与后得之《泰誓》相合而后析为三篇,与其余二十八篇相加,乃为三十一篇之数。至汉宣帝之时,大、小夏侯增立于学官,乃并三篇《泰誓》为一篇,不再分卷,或者衹在两篇之间空一字以为起迄标记,《熹平石经》残石所载《盘庚》上篇“弗可悔”与中篇“般庚作”之间,以圆点作为分篇标记,即是其事。然欧阳《尚书》立学,在汉武帝建元五年,其时后得之《泰誓》未必出,则其经三十二卷,其章句三十一卷者,或刘歆、班固乃自后著录,故其经虽有三十一卷,其篇目仍为二十九篇。否则,欧阳立学之际即有《泰誓》三篇,乃不可解。
据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载,考定汉代大、小夏侯所传习之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之篇目,当如下述:
合今本《舜典》(“慎徽五典”以下之文,无篇首二十八字)之《尧典》第一;合今本《益稷》之《臯陶谟》第二;《禹贡》第三;《甘誓》第四;《汤誓》第五;《盘庚》第六;《高宗肜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泰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范》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诰》第十四;《康诰》第十五;《酒诰》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诰》第十八;《洛诰》第十九;《多士》第二十;《无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诰》之《顾命》第二十五;《费誓》第二十六;《吕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
近人蒋善国认为,以上今文《尚书》之目,也就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之篇目,惟伏生所传之《泰誓》无后得之文,而今文则合新旧《泰誓》之文而后析以为三篇,但其篇目与卷数仍为二十九。这二十九篇,也就是秦始皇焚禁《诗》、《书》时由朝廷所选编的官方《尚书》定本,根本不是秦汉之际亡佚之后的结果。我们则进一步认为,秦代官方编定的这二十九篇《尚书》,其实也是从当时所流传的四十五篇《尚书》,也就是所谓孔壁古文《尚书》之中选定的篇目。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艺文志》也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锺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鲁共王坏宅得书之事,当在景帝初年,兹无须置辩。而孔壁古文《尚书》比伏生今文多十六篇,则总数当为四十五篇。《汉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即孔壁有《书序》一卷可知,故为四十六卷。此十六篇古文篇目当为秦代选编《尚书》所弃之书,而孔安国但依今文隶读古文,却并未为此十六篇遗弃之书作传。其后,古文经学盛行,东汉马融、郑玄及魏王肃注古文《尚书》,亦仅注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而于十六篇遗弃之书皆不为作注。
据《汉志》“得多十六篇”之说,则今古文《尚书》皆有《泰誓》当无所疑。钱大昕《潜研堂答问》说:“《书序》称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纪》所载‘武王上祭于毕’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时,今文《太誓》尚存,而《疏》云‘上篇观兵时事,中、下二篇伐纣时事’,可证《史记》所书本于《太誓》,史公既亲见古文,则今文《太誓》之为真《太誓》审矣!”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则太史公所录《太誓》原文,当为今古文《泰誓》所共有。
因马融致疑于后得之《泰誓》,说:“吾见书传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言。”伪造《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者误读马氏之说,以为马融疑于新旧《泰誓》全文,遂另造《泰誓》三篇,其文无一言与《周本纪》相同,以符合马融所疑后得《泰誓》之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于《尚书》取伪孔传本,则真《泰誓》乃因马融一言而终亡。今传伪孔传本《泰誓》三篇,既非汉代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传之今文《泰誓》,亦非司马迁所见之今古文共有之《泰誓》。
至于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乃缀集《史记》所引《泰誓》之文,以足二十九篇今文之数,其钩沈辑逸之心可鉴,但究非西汉今文之旧,亦非完璧全袠。是以本《释读》虽以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载篇目为序,既不取梅氏伪本《泰誓》之文,亦不取孙氏辑逸之书,故本书仅作二十八篇释读。至于其篇名之用字,见诸载籍者,与孔氏《正义》本有所异同,则皆于各篇【解题】略作辨析,兹不复赘。
【作 者 简 介】

程水金,1957年生,武汉人。文学博士,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多次负责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并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首席专家。撰有《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二、三卷(共五册),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文学、史学及哲学领域皆有较大突破。





